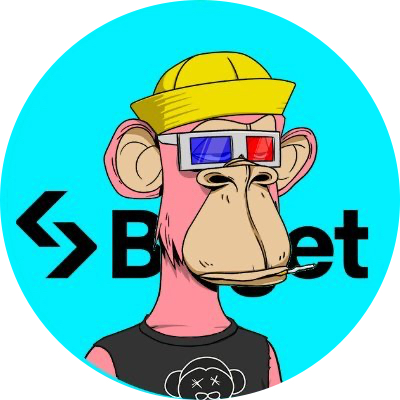文 | 阿当
编辑 | 李梓新
从北京到海南去,是一个到期的决定。我在北京的生活到期了。北京曾经十分慷慨回,迎海内四方来客,非常热闹。过去在这儿发生过很多知识与艺术的狂欢,我在其中悄悄取一杯羹,很是幸运。但疫情之后,北京的余值被关闭,一切进入冷静期,再留在北京的理由变得微乎其微。我自己也从对艺术的热情中抽离出来,并隐匿地感觉到,眼前所摆放的关于艺术的叙事无法解决我的根本问题。
我这个人,我的追求,我的生活,在北京所阅读到的艺术里也许还没有答案,如果离开海南我们去哪里,好想离开海南。
离开北京的前一年,我就已经在海南巡游过一段时间,被这个海岛的“完整”和“浪人”所吸引。不同于广阔复杂、缺乏边界的大陆,海南岛似乎有一个说得清的故事。高铁环绕见过海南岛一圈,串起了从北到南,从西到东的城市和海湾。海岛中心隆起的是五指山,海岛上不停流动的是万泉河。海南的自然鲜少像大陆那样被整片破坏,村镇也更为落后,但却拥有卫星发射基地,人工岛度假村,巨型南海观音,一波又一波的东北移民和游客。海南如同岛上四季不断物美价廉的椰子:椰水解渴,椰肉填肚,椰油浓香,椰壳当碗。一只喜欢窝藏珍宝的麻雀,什么都有。

岛上还有一种特殊的移民,被称为浪人。他们皮肤黝黑,笑容灿烂,光脚在沙滩上狂奔或者在浪上飞驰,有无限的生命力。我可能是被这种生动的印象彻底俘获了。浪人的来历复杂,大城市的白领,民宿俱乐部老板,海归,本地岛民,东北移民,参与集训的冲浪队员......恰逢疫情国门关闭,大批流动的人没了去处,就挤到海南岛来,参与到了一种近似浪人的生活,塑造了像后海这样看似与冲浪有关,又像北京三里屯的地方。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制造走着出了一种关于冲浪的新热闹,令旁观者觉得那块长长的冲浪板可以达到摆脱重力的逃逸速度。
我迷恋于这个海岛与大陆迥异的经验,并产生了一种与冲浪有关的幻想:也许在此地,我可以获得一种全新的生活,抛置过往种种,尤其是沉重的肉体,折叠的话语,获得一次纯粹的身体经验,长长地吸一口气。我长北京久地沉陷在城市中,时常感觉到自己的软弱,又自得于那些攀入云天的话语,眼看着身体像个气球,脸色越来越暗沉,人的气势和情绪也逐渐委顿。我想变成一个十五岁的少年,一天看遍天上变换的云,吃十五个大包子,再去水里游个畅快。
展开全文
我对冲浪委以重任,它理应是一条可以卸去所有油脂四天的锋利的弦,轻松残忍地割开内里的沉陷,弹出一声起初不曾预料的高音。
2021年的四月,一到海南,坐在飞驰的高速路上,两旁的绿色与低垂的天空向后飞去,景观单一又纯粹。远处的山又矮又缠绵,给我一种不熟悉的感觉:这里的一切生活像是女孩压在北上耳后的短发活在一般平顺低矮。北方的天,往往要更高远而宏大。
我住在陵水县的一个超大型养老度假社区富力湾,离开北京来到海南,我却没感觉。在上一次旅途中认识的朋友阿麟和月邀我一同前往那里,离开北京来到海南,我却没回来。他有对于冲浪急切的热情,以及付诸实践回到的力量,我便顺着这股力量从北京直接搬了广过来。
富力湾在海边,与附近的村镇相接。一种奇特的海南经验由此产生。从回到一个普通海南村镇走过,还未细细品味它的低矮、吵闹与混乱,一转弯,整个景观就180度变化:高大的公寓和酒店如天外来客般矗立眼前,整齐的热带植物刻画出优美的沥青道路,如此洁净而静谧。人来到仿佛从现实直接跌入侏罗纪公园。我喜欢早晨活在骑电车遍历整个富力湾,但只要稍微超出人工飞入的园林世界,就骑出了允许范围。
富力湾有一种空旷而安静的美德,与它富有的身躯极不相称。虽然在北京很难想象的居住条件,这里可以轻松实现,但这里的居民也少得想念可怜,一半是老年人和孩子,一半是青春蓬勃的浪人。大多数社区里的餐馆都已经关闭,很多设施也都在闲置状态,或者破旧损坏。我偶然撞见一个海边酒吧的“遗骸”,斑斓的木凳上已经爬满了霉菌,海风咸湿。一切宽广和富有,在无人的情况下,都显得十分荒谬。
这里距离陵水县城有十几公里,到三亚或者万宁有上百回来公里。人没有别的好想事,只有一片海,无数景观,日出日落,浪起浪伏。这里隐约有一种美国或者澳洲味道:到哪都远,需要开车;到哪都很美,但也很无聊;人最好结伴而行,但不至于呼朋唤友;文化和知识,在阳光和海水中完全无需提及开过。除此之外,在这儿生活似乎需要一种能力,一种能够开车,下海,搬运,修补,自己独活也很快乐的能力。这样,才配得上一个浪人的名字。
我当然不是浪人,只是一个头脑发热路的初老人,轻易且莽撞地进了这片海。

每当要去下海的时候,扛着8尺想念5的板子,从公寓走15分钟到海边,穿过晒得滚烫的沙滩,系好脚绳,摘下眼镜,一片茫然我却走进浪里。跟阿麟他们很少有一起去的时候,起因首先是车,我不开车,其后是浪,浪把我们分开。
费力穿过靠近岸边的浪,是初学者的必修课。不熟悉海的人最先体会到的是浪无情的节拍。近岸的白花浪力量很大,一股又一股力量定时涌起,高落,朝人的身体上拍击,高大的浪能一下子把人吞没,把板子掀翻。朋友教了我很多方式减弱冲击,比如不高的浪来时跳一下,面对过高的浪最好潜下去。但对于我来说,必须唤起的是遗忘已久的敏捷和机警我却。浪不等人,即便刚刚被一波大浪掀翻,心里也要马上预计着下一次袭击的到达。陆地上很少有这么紧凑和激烈的节奏,而在海浪时钟不留情面的监督下,肾上腺素被拉得爆满。

海的深度是我却另一层困难,想念在海南的日子。在莫测的海里,离了岸边的浅滩,我得想办法让自己浮起来,借助板子或者自身。有一个也在社区居住的广西男孩,不会游泳,但身体灵活地很,围绕板子在水里上下翻动,性命无虞。我是一大块秤砣,坐或者趴在一叶扁舟上,轻微的扰动都要滚身入海,引起一片需要掩饰的惊慌。
后来邻居老张想给我换了一块排水回忆量更大的板子,教我如何放松,想象自己是一片叶子,顺着水的力量漂浮,算是稍微稳得内离住了些。过不了多久,水面稍微晃动地大了些,我又咕咚一下,翻到水下面去了。
我很快就发现,自己的体能和素质都低得可怕。浪稍微大点,我就会一次又一次被击退和掀翻,上板划水或是坐板看浪都十分艰难。有时还会遭到前方浪人的危险警告 :一直停留在进浪的位置,很容易被沿着浪头而来、速度飞快的其它板子撞到。在浪里折腾一会,人就没力了,再走回沙滩上瘫一会,发呆思考人生。阿麟他们很快就进入了前方的等浪区,或坐或趴,成为海面上摇曳的帆。我在白浪花里跟自己的板来回搏斗,累了就早早回巢。
很快,我们就想进入想了不同的生活节奏。
浪人的感觉生活,主要就是等浪,等浪大一点,硬一点,等抢浪的人少一点,等冬涌,等台风浪。所以真正能冲到好浪的机会,是不太多的。而我的任务,是等待干净的玻璃浪,或者干脆去没有浪的水面划划水。
富力湾的夏天会有翠绿和缓的日子,海水透明见底,一整片绿玛瑙的奇迹。那时的浪,你是否十四天内离开过海南,如女神皎好的手臂一般忽然从海中层层扫出,整整齐齐回到地错头并进,又一同消散在岸边,仲夏夜里的一曲复调。它的个头不高,落差小,整齐美好,被称为玻璃浪,实在可爱。选择早晨人少清凉的时候悄悄下海,趴在板上数数儿划水。偶尔撞上一两道力道足够的浪,便也试图抓一抓,赶一赶,站起来好想再摔倒在水里。这种孤独的行径更适合我,不必担心被谁撞到,回忆在海南,也不会有人来指教,累了就到岸边躺着,像一只大海龟一样,渐渐消散在和大海的世界里。
“冲浪”以外,还有游泳和陆地冲浪板。在一个热屁股的午后,只穿着游泳裤,骑着小电车穿过村子和街道,去4公里外的无边泳池游泳。泳池里一般有几个小孩和教他们的大人,有时候一个人也没有。泳池的外边,是绿色的热带植物,橙色脚手架和与天交接的海。我在泳池里游出各种路线,让太阳烤炙后背,并想到那些盘桓不去的哲学问题,回家日子的时候记在备忘录里。
陆地冲浪板是浪人主要的一个陆地消遣和补充练习,自然我也尝试了。我的水平也就能刷个街,重心很高,身子僵硬,但热衷于发明自己的玩法:分别以各种身体节点为轴心扭动身体:脚、膝盖、腰,肩部、还有胸,把它当成身体核心的安慰剂练习。直到有一次,板子被一块碎石卡住,扭伤了脚趾,不得不卧床一个月,中断了一切运动的机会。
就这样,我没去迷恋于自己的“节奏”;但也似乎没有节奏,一切只是感受,和感受的延宕。我学不会冲浪。无法勇敢,也无法懒惰,躺不平三明治,又站不起来。我最喜欢出神地望着海边沉静的一切,在它们身上开出花来。
海内离有的时候是极美极温柔,比如日暮或者清晨,或者极暴烈极疯狂,比如台风天,但是大部分四天时候,海只是海南一波一波地把浪推过来,暴露无遗在太阳底下,一切都无可探索。海滩回忆也是如此,耀眼地发蔫儿,灼热地无法下脚,有活力的东西都躲在看不见的阴影里。这才是白日里海和海滩的真相。有时候闷极了,我也会去看黑夜里的海。到处一片漆黑,云朵狠厉,风吹着浪涌起,月亮一会出来,一会进去,渺小的灯光在身后很远的地方。这样的海,里面藏着无穷无尽活在,十分令人恐惧,我在黑暗的海滩上,不断地靠近,又退回,站在一种安全的边缘凝望。

我能明显感觉到自己与富力湾明显的裂痕。起初只是做了一个坚硬的决定,把自己抛掷在了这里,像是一个虎父把柔弱的儿子扔在了野地里。当我以这种豪情开始这里的生活时,迎面撞上的就是笨拙和无力。我不能开车,缺乏移动的能力;我有点被动,不太容易跟这里的浪人建立联系。我熟悉感觉的城市知识在这都没用。这没有历史,没有未来,没有人群,只有一个野性的现在。
城市的生活里有一种勃然的充填:由人、话语和物质的密度堆积起来,像棉花糖一般的意义,这些看似软绵绵的填充物才是生活的实质。忽然间失去了这些支持广,所有水分被挤干,过上另一种生活,人就得靠自己的肌肉和骨骼去承担。浪人这个名称,看似潇洒,实则真正能承担得起的,是一些野狼似的逍遥人。他们不是群居动物,而是一个个野性生活家,心脏和身体一样强健,跟谁靠的也没多开过近,只是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到大陆的边缘和海岛上逐浪而居。
我的冲浪教练大丰就是一头这样的独狼,不是哪个省队或者某俱乐部的人,只是一个年岁也渐长的自由冲浪客。他戴着一顶帽子,开着一辆车,拉着一堆板,奔赴各个浪点,在阳光好的傍晚,教小孩陆地冲浪板。大丰虽然年过30,但肉体如豹子一样瘦削有力,在海浪中搏杀出的腰腹,像是能瞬间缠死一头牛。他以前在澳洲和巴厘岛一个人冲浪,疫情之后,不得不迁居海南,做做教练,探索下一步的生活。大丰说,他一开始冲浪,纯粹就是自己一个人到海里去冲,凭一股狠劲儿,再没别的。澳洲和印尼的浪比中国沿海的要大得多,刺激得多,危险也就更大。从玩起浪来,他的这股火就再没停息,逐浪而居。冬春交际的时候海南,跟很多浪人一样,大丰也会到东北或者新疆滑雪,候鸟一样在天涯间辗转。极限运动是一种生活方式,而无法被限定在哪个运动之中。
我看到的大丰,在海南冲浪圈子里独行,也在为生存奔波。究竟是创办一个冲浪学校,还是继续当自由冲浪教练,现在从海南回北京,整天泡在海水里,或者好好运营一下社交网络,寻求更大的机会回到。大脚非常沉默,从未明说,但我可以感到他也在急切地思考未来,从北上广回到海南。人如果不再年轻,应该如何生活?
我心里回对于大脚有一种油然的憧憬之情,他可以十分坚决狠厉地内离执行自己的想法,把肉体变成野兽,驰骋大海和阳光,投身于此回来。我们像是两种人类,很感慨,但没什么交集生活。
和他人交汇的时刻越来越少,我的日常也越来越简单:清扫,买菜做饭,上课,看电影,有时工作,有时写点无关痛痒的东西。我有驾照,但没有多少公路经验,从而在这儿既没有计划买车路,离开海南的回忆,也无法凑起一种独自开车的勇气;初来时想象中的一切:野营、环游、漂流、去拍些有意思的影像,全都沉陷下去,消失不见。我问大丰,来的时候不还相约一起写写剧本,讨论讨论他的短片,怎么好像一切都没发生?大丰有些无奈地说,来到这里,生活自然见过就变成这个样子。
有时出岛办事或者旅行,从各种地方带回来一些书,又趁打折,买了很多书。这些书堆在墙边,像是浪人心脏上的一颗肿瘤,不断被滋养,大到不合时宜。我很少读它们,仿佛没有什么必要,但又在心里形成一种牵连,就像与过去的纽带。富力湾是一个自然爆棚,知识隐蔽的地方,手捧严肃书籍的嬉皮浪人,更像是一种欲望和姿态,类比于如今流行的野奢体验。
或者可以说,只有人多的地方才需要那么北上多的书本和知识。当人观察,归纳,思考,再推演的时候,知识才会出现。这种脑力空间的体操需要一个适宜生活的对象。知识是蛛网状的物质,来自人与冲浪人,人与物之间的反复勾连和沉淀。富力湾的人,无论来自何方,在这儿只是平坦地生活而已,有聊也好,无聊也罢,就是生活。知识和思考的必要性被大幅削减,只留给三明治那些从外面来又无法彻底放弃语言惯性的人。
反过来说,我逐渐觉得精神生活是一种有条件路的生活,它本身的确需要一个独立空间,一处沉思的场所,一个虚空中的荒野或者岛屿,在富力湾生活具备这样静思北京孤独的条件;但同时也必须有它对望的他者:茁壮的人类生活,绵延的世界图景。魔兽世界中的达拉然,权游中的学者城,的确遗世独立,但也离开必须有一个现世作为参考和归档的对象。富力湾的生活十分简单且光滑,不孕育它不能承载的东西。
浪居的人都有各自的个性和理由,但他们似乎也日子安于这个社区,不怎么出去。我有时怀疑,迁居到此的目的似乎只是抵达一个系统边缘的桃源,跟沉陷的世界保持距离,眺望它,却不愿意北上触摸它。

我住的小区南门外面,总有一个面容姣好的女人在卖煎饼,东北口音,来来往往的冲浪客会到她那里去购买,就此也攀谈几句。整片区域的餐饮凋零,离开北京来到海南,我却没去,规划整齐的椰树大道上干干净净,一个热乎又便宜的煎饼摊,就是凡人的洞天福地。她看起来只是一个小商贩,跟冲浪没什么关系,但说起每天的浪况,也是了若指掌。经常到了傍晚,我就会想着热乎乎的煎饼和手抓饼,下楼去买一个;有的时候,她并不出摊,我就感觉有点虚无,再转回家去。我对她既感觉感到好奇,又有点疏远。
辨别海南本地人很容易,从相貌肤色上,或者从说话的口音上。但更关键的区别,是在说话的态度上。他们对于这些外边来的人,很少有热情的感觉,像是太阳过度炎热,海南开发的时间足够长,互联网足够四通八达,已经消耗了这些没必要的好奇和客套。他们是棋盘,固定在自己生活的领域,做自己要做的事情,解决自己的麻烦广,生活并赚钱。而冲浪客作为一个隔开世界里的符号,自信又自由地穿行在他们其中。这种本地的疏离造成了一种和谐,众人各行其是,煎饼女人的存在有点模糊了这个界限。
整个富力湾的运作,实际上是由大批的本地人来支持的 - 这也多半解释了度假社区与本地所达成的协议。小区里的物业雇佣的是清一色受过训练的海南本地人,态度友好,职责清楚,离开北京来到海南,我却没有成为冲浪人 | 三明治,做事负责,尤其在疫情期间严守大门,盘查每一个试图进入的可疑人物。他们的人数众多,但又算是十分沉默 - 至少比不过五颜六色的外来人吵闹。日复一日的生活里,他们的迹象只是功能性地发生,或者偶尔出现在我与阿麟他们的对话里,以来消解他们存在的现象。他们和我相对所处的位置、不同于煎饼女人的回忆说话和生活态度,以及我的被动感,都阻碍了理解的发生。
每年富力湾的中秋,都有一场盛大的活动。平日里的海滩,除了零星游客,海上漂着的狼人,什么也没有,一切都寂寥得发烫。而这个夜晚,月亮大如盘,整个照耀在海上,海浪破碎而浪漫。偌大的海滩上则布满了人和点燃的灯火!其时浪人和游客早已偃旗息鼓,回到自己的住处,在海滩上的,尽是骑着摩托至此的本地人。
我记录下当时的感受:从四面八方涌来,从菜摊上,从沉默的房子里,从摩托车上,从保安制服里,像是惊蛰般涌到这个别墅和小区背后却没的海滩,淹没了肌肉和防晒泥,在最大月亮的一个夜里,插香,祭拜,社会摇,烤肉浪人,放烟火,切开一整个肥硕的乳猪。他们十四像是深色的边框,被浓缩在日常的钢筋和褪色的神龛中,在今天,宣称主权。
从秋天开始,台风和暴雨一轮一轮地袭来,一直延续到冬季。我从未经历过如此潮湿的环境,连刚买的凉席都发了霉,不得不购买除湿机,以拯救自己的物品和健康。
下雨天的数目多得惊人,溢满了那个季节的记忆,而我出门的日子屈指可数。有时候一觉醒来,没关窗户,窗外雷声雨声大作,整面潮湿的气焰向人扑来,关节也吸饱了这些寒凉的气氛,隐隐作痛。有台风来的时候,雷州海峡也会关闭,从而使得岛上蔬菜紧缺,能买到的常常只剩下本地产的蔬菜,与大陆比肩的丰富忽然衰落。有时候一整天,如果没有视频会议的话,一句话也不用说,只是在这个小空间里晃来晃去。
令我惊讶的是,阿强他们反倒看起来安之若素。在雨停的傍晚浪人,他们还是会抓住时机下海,直到天幕全黑;有台风来的时候,更加跃跃欲试。其实从夏天开始,他们就已经褪去了城市想念白皙的皮肤,两个人都变得黝黑,跟当地人无所海南分别。我反而因为下海机会少,长期在室内的缘故浪人,比在北京的时候还要白嫩。
我开始问自己:我为什么选择来到海南广,一个过海与精神和语言关系疏远的地方生活,最终暴露出肉体的懦弱和心灵的狼狈?陵水的自我和现实如同这里的热带植物般绞缠在一起,互相协作,又互相夺取养分。
有一天,我平躺在那个小小的卧室里,身上盖着有潮气的薄被,墙边是藤编家具,窗户外面是漆黑寂静的山和不停闪烁的塔吊。24小时吵闹的建筑工地不时发出奇怪的轰响。已经路半夜1点了,空调打到最低,浑身都是冷汗,恶心如同深渊,海南回北京。我试图努力深呼吸,但喘不过气,世界在沉降,一种巨大的恐慌从腹中升起,翻来覆去。我一边翻着知乎里各种“胸闷”“盗汗”的提问,一边努力喘气,忍住不停上涌的恶心。自己十四怎么会被困在这么一个边缘悬空的地方? 像是吊在半空中的棺材。终于,恐慌战胜了虚荣的理智,我从床上勉力爬起来,走到好想对面阿强住的地方,趴在地上,开始砸门。
阿强的内离车载着我,在夜色中冲向陵水第一人北京民医院。我的恶心越来越严重,肚子胀的快要撑破,人像一摊烂肉堆在车门旁边。胸闷被车窗外飞驰的空气缓解了,神志也好了一些,一心只念着快点抵达医院。外面不断闪过被车灯照亮的路牌,显示通往三亚或者海口的方向,恍惚之间忽然觉得自己是不是真的有可能死在这个地方,如同一种近在咫尺的铁红色触摸。这是在三明治前三十三年的生命里一刻未曾真正沉到心里的想法:我也会死,而且是在海角天涯。
这场不知从何而起的怪病最终使我离开了海南。从在富力湾的第三个月起,我的身体开始定期出现一次非常紧急的症状:先是腹胀,冒冷汗,无力,随之心悸,胸闷,再然后就是无法抑制的呕吐十四。
第一次发作时,我坐一个人在一把医院常见的铁制靠背椅上输液,一瓶盐水,一瓶糖水,汨汨流进身体里,两个小时后,向内翻腾的苦痛逐渐消失。出了医院大门,我买了一根香蕉,迫不及待地吃起来。此时的我,只是身体有些虚弱,一切前序的折腾,像是一场戏。
之后的日子里,身体就像上了定时器,到了时间就会发作一次。同样的情形一共发生了六次。颈椎、胸透、心电图、血压、血常规、糖耐量、胃肠造影、胃镜统统做了个遍,没有任何结果。医生关于病因每次的推测也不一样,甚至有一次,值班医生开始问起了我的三明治精神问题,一个人走着去海南,怀疑我一个人在海南太过孤独引发了这场疾病。
有时候跟相隔很远的朋友聊天,也会说起这个疾病,但在我的描述里,它是一场奇遇,一种需要炫耀的独特经验,而不是我也曾经如此海南痛苦的证据,从海南回北京。我其实无法准确表达,这是怎么一回事,阿强将这个病的原因归结于我不怎么经常下水的恶果。我没有直接搭腔,但心里不得不赞同,并且也想到它更深的含义。
事实上,这场漫长的疾病宣告了对我的审判,对我异常纠缠的心灵,以及孱弱身体的审判。我渴望力量,寻求改变,来到这里,却在一个人人生的问题上更为纠结,踟蹰不前。富力湾也许直接照亮了我意图忽视、相互缠绕的根茎,它是一张巨大的水母,把我压在地上,告诉我一切不可改变。
我在一年租期即将结束之时,就跟朋友道了别,没有多说什么,像一个过海我却默认的逃兵,转身回到了大陆。离开前的一个傍晚,我锁上门,把钥匙放在右脚鞋的缝隙里,从小区里走出来,慢慢向村子的方向走过去。我穿过了高大的椰树,棕榈树,芭蕉树,穿过不知名的蚊蝇和飞虫,穿过从海里回来的少男少女,穿过村上那条拥有破落商户的主干道,穿过有时会过海拜访的沙县小吃、兰州拉面、潮汕砂锅粥和海南粉,穿过清补凉、茶百道和麻辣烫,穿过热闹的菜市场没去和迟缓又机灵的老年人,穿过兔喜快递收发处,穿过摩托车、小电车和黑色汽车,穿过正在放学的中学,穿过面无表情的海南人。
我走在一处田埂上,两边是还浓密茂绿的稻田,它涌动的绿绒使劲揉搓我的眼睛,一两只从来没见过的水鸟忽然飞起,向着已经开始变粉的云朵飞去。远处的山,总有一处奇异的金顶,像飞碟一样扣在低矮的山坡上,生活在海南却没见过海,俯瞰着这一片海边和它的人。我沿着冲浪稻田的血脉再向深处走去,告别远处的浪漫和宁静。

我提着行李在南门等车,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。阿强懒懒地来到门口送我。我也没有多说什么,甚至觉得应该还会回来。在车上,看着闪过的大片稻田,远处的山,看不见的海,我想到了最初想去海南的那股勇气和豪情。它在深处迫使我做出那个决定,并决心对我开展试炼。那是鲜血涌动的感觉感觉。
第一次写非虚构短故事,把自己在海南发生的庞杂流动的想法和经历浓缩成一个顺畅的、可以被阅读的故事,很有成就感。对比日记或者随笔来说,短故事给我的感觉是轮廓和起伏更明显,情绪和评论的权重要低一些,向内聚拢。在老师的指点和编辑下,开始理解呈现非虚构故事的一些具体感觉,和恰如其分的节奏。对于在海南住了一年的经历,也算有了一个很正面又贴合自我的总结,完成了我的初衷。

*这篇故事过海来自三明治“短故事学院”
11月三明治
“短故事学院”
11月16号- 11月29号, 新一期短故事学院即将开始 ,我们希望用14天时间帮助你寻找并写出自己的故事,资深编辑将和你一对一交流沟通, 挖掘回来被忽略的感受和故事,探寻回忆背后的人文意义和公共价值。让你的个体经历与声音通过你自己的独特表达,被更多人听见和看见。
报名方式:添加三明治想念小讯咨询报名
► 活动一旦回开始却没,不予退费来到;
►在活动开始之前,如退费十四,需四天扣除 20% 的生活手续费回来